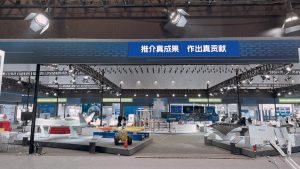2024年05月30日

西交利物浦大学影视艺术学院大楼的电影院里出现了一幕罕见的场景。荧幕上播放着画面,但所有观众都闭上眼睛,在静静聆听着旁白。
导演刘雪涛怀揣着忐忑的心情坐在观众中间。这是她和团队一起制作的无障碍纪录片,而现场观众正在体验视障者是如何“观看”电影的。
刘雪涛是西浦影视摄影与制作专业的一名大四学生,由她作为队长带领的调研项目荣获“南风窗·调研中国”的年度冠军后,回到学院举办放映交流会。她怀着一种创作者的“煎熬”,尤其当作品展现在本专业同学面前时,她感觉到不自信,甚至有一种“羞耻”。

(在影视艺术学院举办的“南风窗·调研中国”放映交流会)
在刘雪涛看来,从小到大,她并非传统意义上成绩特别出色的“好学生”。但在西浦的多元机遇中,她重新建立了自我认知。以下来自刘雪涛的自述,带你观看一部关于她的个人影片。
CUT #1 学习线:第一次接触人类学,决定理转文
我们家几代人都是学理科的。进了重点高中的次重点理科班,我拼劲全力学理科。可说实话,就算能维持中等的成绩,还是不太喜欢。
高二暑假,我报名了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UBC)的夏校,决定去外面看一看。一次课外活动中,我参观了当地的一个人类学博物馆。博物馆里陈列的是和种族、殖民史相关的内容,讲生命,讲人类的文明、历史和发展。
这是我第一次接触人类学。平时生活中只有学习、吃喝拉撒这些日常小事,突然面对人类文明如此宏大的命题,我被触动了。

(刘雪涛参加UBC夏校)
从夏校回来后,我确定自己的兴趣点是在文科方面,顶住压力从理科转到了文科。夏校的经历也让我知道自己更适合自主、开放的教学氛围,所以我同时开始考雅思、申请UBC。
2020年初疫情爆发,在家上网课的时候,我收到了UBC的offer(含奖学金)。面对疫情带来的不确定性,最终我决定留在国内,备战高考。
CUT #2 公益线:18岁生日那天,武汉封城,我得做点什么
2020年1月23日,武汉封城,那天正好是我18岁的生日。我感觉自己必须做点什么!看到朋友圈有公益机构在招募线上志愿者,我毫不犹豫就加入了。
我害怕别人会因为我是个高中生而不信任我,所以我没有透露自己的真实身份,一直尽力在“装大人”。我们的工作是寻找一些物资并对接捐赠方和需求方,最后把物资精准对接给了全国100多家医院。随着我工作得越来越带劲,最后做到了团队的核心成员之一。我“装大人”“装”得不错,直到工作结束,他们才知道我是个学生。
大一暑假,河南发生洪灾,之前抗疫的群里又活跃起来,很多人发出求救。这次,我担任了队长的角色,组建了一个1000多人的线上志愿者团队,为救援团队对接物资,也为线下志愿者们对接食物。

(疫情期间,刘雪涛参与的公益团队收到的感谢信)
CUT #3 学习线:“科技不耐受”,纪录片成为我的舒适区
大一进入西浦,我兴奋地选了几乎所有专业的体验课,从商科到建筑学,什么都想尝试。最后选择了影视摄影与制作专业,是因为一直以来我都有一个目标,那就是“看世界,并且发声”。不管是新闻还是电影,都是我输出的一种工具。而且在我看来,电影具有超越文字的传播力量。
我是个有点排斥科技的人。我不喜欢用手机,同学都用平板电脑记笔记,我到现在都是用纸笔。大二进入专业课,现实给了我致命一击——“科技不耐受”的我面对摄影机、灯光、录音装置这些高科技设备,完全摸不着头脑。我在电影制作方面的能力实在太差了!
就在我几乎要对自己失去信心的时候,我遇到了教纪录片课的王凯思(Tracy)老师。她鼓励我尝试纪录片制作。在她的指导下,我惊喜地发现,纪录片更注重真实性以及情感的表达,不需要过分依赖复杂的拍摄技巧和高科技设备。这种创作方式是我可以掌握的,我找到了自己的舒适区。虽然还没有那么擅长,但我很喜欢,也希望做得更好。

(左为王凯思老师)
大三那年,我以苏州一家按摩店老板为主角拍摄了一部关注视障群体就业的纪录片。在之后的社会实践中,我也用纪录片的形式捕捉了一些真实的角落,记录着和我们处在同一片蓝天下的人们的不同命运和人生。
通过纪录片,我真的实现了选择影视专业的初衷——用影像发声!

(调研纪录片剧照)
CUT #4 学习/公益混剪:走出象牙塔,看看真实的世界
我想分享一个特别的手机聊天记录。

这是我们23年暑假做视障调研时建的群,团队中有我的一位视障好友樊文谦。在他进群以后,大家都会坚持做到用文字描述每一个表情包和图片的聊天方式。
我的朋友圈也是这样。我的微信好友中有一位田野调查时认识的视障奶奶,她用读屏软件读取我朋友圈的内容后对我说:“小刘,看文字知道你很开心,虽然不知道9张图里是什么,但是奶奶祝你天天开心。”自那以后,我就会把每张图都在朋友圈的评论里做一个详细的解说,奶奶还会给我点赞、评论,特别可爱。

自2022起,我连续两年参与了南风窗主办的“调研中国”公益项目,深入实践了人类学研究中我最喜欢、也最擅长的部分——田野调查。第一年,我作为团队成员,对性别视角下的城乡养老这一议题进行调研,采访了绍兴市165位老年人;第二年,我作为队长,带领团队聚焦“视力障碍人士的生活技能掌握与社会融合”,采访了35名视障人士。两次调研,我都制作了纪录片。


(刘雪涛参加“白手杖盲童之家”的活动)
采访视障人士之前,我会做很多功课,我会去了解视力障碍的不同等级、造成的因素,以及如何定义“残障”;我会搜索相关的新闻和政策,也会向公益组织学习相关的知识,比如见面时应该怎样去合理地搀扶他们……我也做了很长时间的心理建设,因为作为健视者,我们难免会带着某种“同情”的心态。当我觉得自己没有办法保证平视他们的情况下,我就不会去开始。所以采访他们时,他们都会觉得我还挺不一样的。

(刘雪涛与被采访者)
CUT #5 导演独白:做公益的意义是什么?
做公益,说实话,我时常会陷入内耗,有时感觉“喘不上气”。就像那次抗洪救灾,每天忙于找物资、协调各方,还要应对网络上各种复杂的信息,害怕被人质疑、遇到骗子,每天战战兢兢。
接触弱势群体,和他们共情,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挑战。有一次,我在电话中采访一位视障女孩,她说小时候觉得自己很漂亮,但因为后天失明,她连自己的样子都忘记了。为此我思考了很久,有很多感触。
为了进行阿尔兹海默症患者的相关研究,我每两周都会去拜访一个患者家庭。患者奶奶有时会把我误认为她的女儿,拉着我的手哭,每次回来我都会特别低落……

后来我意识到,我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处境和命运而感到难过,更多是源于一种无力感。就像获得了“调研中国”第一名后,我觉得并没有给视障群体带来实质性的帮助。
直到有一次,跟室友出去吃宵夜时,我低头系鞋带,抬头看到室友在盲道挪动共享单车;再后来,朋友提到药盒上没有盲文的问题——他们无形中给了我一种反馈,那一刻我有种奇妙的感觉:
原来我所做的确实有影响到一些人,引起了他们的关注,而他们可能就会影响到更多人。
CUT #6后记:我想成为一个有担当的世界公民
放映会结束后,很多同学都跑来和我交流。有同学肯定了我影片中的情感联结和情绪张力。还有同学说,会去关注相关的议题,也想做相关的纪录片。这让我又意外又开心。
目前,我正在以年为单位拍摄一部关于视障高中生小迟的纪录片,这也是我的毕业作品。期望通过这部作品,让更多人走进小迟的世界,也为她打开一扇通往更广阔未来的窗户。

(刘雪涛和小迟)
过去的经历让我认识到,后疫情时代,人与人的联结和情感是多么重要,我也逐渐发现了“看见”的力量。毕业后我将在香港大学继续新闻学纪录片专业的学习。
未来,无论通过什么形式,我仍旧希望自己能够去行动、去改变,希望自己的声音被听见,也希望自己关注的议题被看见。
很幸运,在西浦,我找到了真实的、不被定义的自己。作为一名西浦学子,我也将继续努力,成为一个有担当的世界公民。
(记者:李雯祯 编辑:石露芸 摄影:王左夫 部分图片提供:刘雪涛)
2024年05月30日